那个周末的午后,阳光,阳光像往常一样斜斜地照进堂屋。爷爷的木匣子空着——扑克牌不见了。
这本该是雷打不动的扑克时间。自从奶奶走后,每个周末下午,爷爷都会取出那副磨出毛边的扑克牌,我和哥哥轮流陪他玩“争上游”。输的人在额头贴纸条,爷爷额上的皱纹里总是夹着最多的白条,可他笑得最大声。
可今天,扑克牌不知被谁收走了。哥哥翻箱倒柜,我在每个抽屉里摸索,爷爷坐在他的藤椅里,眼神有些空。没有了那五十四张纸牌,时间突然变得很重,重得能听见墙上老钟的每一次滴答。
“要不……看电视?”哥哥试探着问。没人响应。
后来不知怎么开始的,爷爷讲起了他和奶奶的故事。他说奶奶年轻时辫子又黑又长,说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村头的打谷场上,说他这辈子这辈子最得意的事,就是用一个月的工分给奶奶换了块红头巾。这些故事,在以往洗牌发牌的哗啦声里,从来没有机会说出来。
我注意到爷爷的手——那双曾经娴熟地弹洗扑克的手,在空荡荡的膝盖上微微颤抖。我突然明白,扑克牌不过是个借口,他真正需要的,是有人坐在身边,是让周末的时光不至于太过漫长。
哥哥默默起身,从作业本上撕下纸条,蘸了点水,贴在爷爷光洁的额头上:“爷爷,你输了,该你讲故事。”爷爷愣了一下,然后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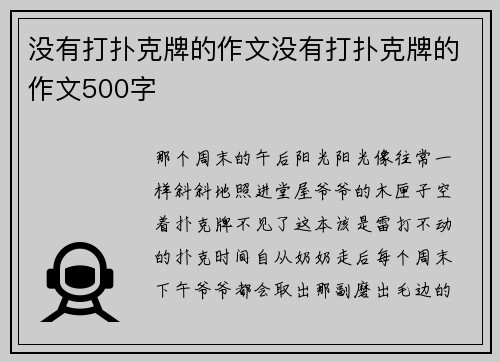
那天我们没找到扑克牌,却找到了比王牌更大的东西。当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,我看见空木匣里装满了另一种东西——它没有红心黑桃,却让整个下午闪闪发光。
悟空黑桃A原来,最深沉的陪伴,恰恰发生在所有道具都缺席都缺席的时刻。就像爷爷最后说的:“扑克牌会旧,会丢,可你们坐在这里的时间,都攒在我心里了。”
那一刻我懂了:真正珍贵的,从来都不是我们手里握着的牌,而是愿意陪我们打完每一局的人。
